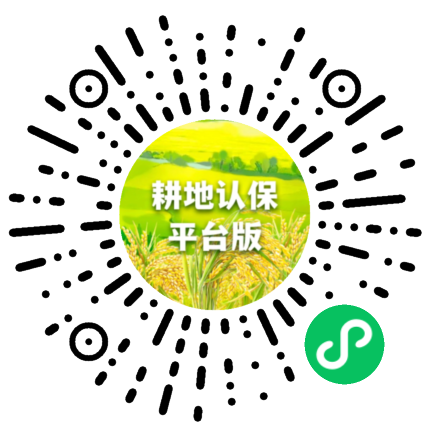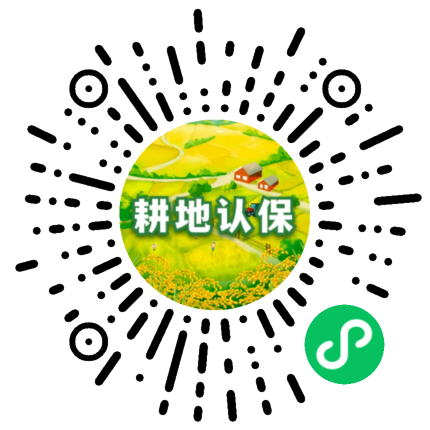背景
耕地是提供粮食安全保障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自然资源条件。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人口逐步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逐年减少。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2021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强调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且必须是良田”[1]。
我国是一个人口超14亿的大国,根据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我国耕地面积为19.179亿亩,人地矛盾突出、空间分布差异大是我国耕地的两个主要特点。广东省作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省,在守住耕地红线方面压力较大。尤其是粤东的潮汕地区,历来是广东省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294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为0.17亩/人,而广东省平均人口密度687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0.31亩/人,可见潮汕地区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潮汕地区境内河流众多,有韩江、榕江、练江、龙江和黄冈河等,有丰富水源和较为肥沃的土壤,历史上是农业生产的发达地区。过去,因人均耕地少,为获得更高的产量,农民会在耕地上投放更多的劳动力,“种田如绣花”是对潮汕地区农业生产最生动的形容。
但是,随着近年来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劳动人口转向第二、三产业、农村人口减少、耕作地周边环境变化等因素,潮汕地区部分耕地存在无人耕作的撂荒现象。这种情况给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耕地作为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源,撂荒的耕地将无法得到经济产出,对农村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不利于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耕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耕地“非农化”的原因浅析
耕地“非农化”指在耕地上从事非农业活动,驱动其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国内研究普遍认为,非农用地的增长需求、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土地权属不明确以及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是非农化的主要原因[2]。
1、非农建设用地剧增加快了耕地“过度非农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加,从“九五”(1996-2000年)计划开始,我国土地征用速度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十五”计划期间,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大力发展,城市交通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导致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占用。1997-2005年,我国大陆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1亿亩,造成耕地“过度非农化”,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性障碍。由此引发了诸如征地制度、征地收益、补偿标准、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农民非农化加剧了耕地“非农化”
“非农化”狭义上可解释为农民非农化,即农民身份向非农民身份的转变,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3]。农民因农资成本投入高于粮食价位上涨幅度,农业补偿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逐步下滑,从事农业所得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农民逐渐非农化。体现在劳动力外流致耕地撂荒、利用农地从事非农业的生产活动等现象,是社会经济客观条件与农民主观意识层面的一般反应,是耕地“非农化”现象加剧的原因之一。
耕地非农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行政执法监管不力致使占用耕地违法建设情况屡禁不止。农村地区土地违法现象比较突出,存在执法难度大、相关违法人员不配合、基层执法人员态度消极等问题。
(2)耕地质量恶化是农地非农化的隐形原因。随着工农业持续发展,农业化肥过度使用、工业排放污染及耕地“占优补优”落实不到位等现象逐渐对耕地质量造成难以察觉的破坏。灌溉设施老化、自然灾害破坏等自然因素亦可以无形中影响耕地质量。伴随耕地质量恶化而导致的产能下降、土地撂荒,成为耕地保护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3)土地承包制度中存在负面影响。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8年,国家部分地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初步探索,1984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确定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1999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首次将30年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写进法律。现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随着人地矛盾逐渐深化,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耕地保护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农村土地经营细碎化、分散化,不利于快速农业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农地非农化。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农村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因缺少流转、行政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共同作用下导致违法改变土地用途,占用耕地进行非农建设现象在农村地区比较突出。
二、盘活耕地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介绍
为了提高耕地活力,应对耕地“非农化”现象,解决农村劳动力减少、传统种植比较效益偏低、抗风险能力低以及农村土地经营细碎化、分散化的问题,潮州市正积极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仙洲村
仙洲村有耕地约4950亩,土地条件良好,村民能耕善种。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里开始种植大蒜、芹菜等农产品,良好的种植条件和优良的产品使其成为饶平县第一个菜篮子工程的生产基地。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种植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短板日益凸显。由于耕地的使用者分散,每户的耕地零碎,村民开始放弃耕作,农村劳动力向周边城镇转移,导致部分耕地撂荒。
为改变这种耕地撂荒的局面,仙洲村大胆创新,提出“集体+农户”的改造模式,把60亩耕地从100多户农户中流转出来,引入大棚种植如螺丝椒、虎皮椒和西芹等蔬菜,使该片区成为了农业产业基地示范园,并且入选了“广东省十大最具影响力农业农村改革案例”。
仙洲村以“集体+农户”的模式对耕地进行统一集约化经营,同时鼓励当地村民以“带地、带资、带工”等方式入股,也承诺了保底的收益,风险由村党委兜底承担。部分仙洲村村民表示,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村民对流转自己的耕地有顾虑,对土地统一后不知如何处置,但后来因上述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的成功,村民纷纷表示认可该改造模式。一方面盘活了村里的耕地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村民收入,加快了贫困户脱贫进度,对饶平县撂荒地整治和土地流转起到了示范作用。

图1 仙洲村耕地流转前

图2 仙洲村耕地流转后
2. 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东四村
东凤镇东四村的一片耕地约300多亩,其中的200多亩分到500多户农户手中,耕地使用权零散,呈现出一户一沟、一家一垄的状况。因各种原因,该片耕地少有人耕种,呈现出撂荒的状态。为了改变耕地撂荒的状态,东四村积极探索各种措施,充分发挥耕地作为农村重要生产资源的作用,将该片耕地统一进行流转,配合土地整治措施,对田间道路进行重新建设,对沟渠等水利设施进行疏通和完善。引进专业合作社对整治后的耕地进行集约经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例如,果蔬专业合作社采用密种和修剪等改良的种植方式,把传统的番茄种植由每亩350株提高到了每亩1200株。先进的种植技术配合种植优良的品种,使番茄的亩产大大提高,价格也比传统种植的品种高,从而提高了整片耕地的经济效益。
3. 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洋光村
江东镇洋光村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了专业的蔬菜基地,由专业的农业公司种植超过十种的蔬菜。农业公司通过与周边村民共享基础设施,集中销售村民散种的农产品,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采摘储存、再到销售环节的全流程服务,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在田间地头设立的工夫茶座,来自周边的游客享受田园风光的同时,也能品尝到地道的工夫茶,共享农业公司和农户种植的新鲜农产品和如萝卜干、酸菜等农副产品。该模式的收入由村里的土地所有者、提供服务的村民和企业按比例分成,实现了互惠共利,为村民增收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三、经验总结及建议
1. 鼓励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制度
潮州市几个成功盘活耕地的案例可以看出,关键在于进行了土地流转,把零散的耕地进行规整,激发耕地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今后的耕地保护工作中,应鼓励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方式。要因地制宜制定政策,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承包土地、投身农业生产,从事良种繁育、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为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生机和活力;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杜绝耕地撂荒的现象。对抛荒耕地应尽早复垦复耕,优先安排土地流转。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要切实按照相法律法规要求,管护好流转耕地,不断提升地力。对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或其他原因致使耕作确有困难的农户,可以采取长期转租、季节性转租、耕地入股等耕地流转利用办法,签订托管协议,交给有条件的耕作企业或个人集中经营,也可以交由村集体,签订协议实行托管经营。
2. 加大政策宣传推广,提高农民积极性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基层领导和基层经营机构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应积极构建基层服务队伍,加强各层级的管理和信息发布[4],让更多村民了解有关的土地政策、了解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规定以及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使村民更主动参与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来,从而盘活耕地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3. 加强土地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
应统筹考虑综合连片实施整理和开发耕地。因地制宜地进行耕地的改造设计方案,可参《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NY/T 2148-2012)进行建设,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提倡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等。通过科学规划、配套农业基础设施,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的综合产能[5]。加强土壤环境监测和污染防治工程,对农业废弃物进行有计划地集中处理,减少浪费和污染。
参考文献
[1] 刘少华.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01-13.
[2] 袁晓妮, 鲁春阳, 吕开云,等. 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进展及展望[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6.
[3] 朱信凯. 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J]. 中国软科学, 2005(1):7.
[4] 晏意华, 郑向东.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及其对策 [J]. 南方论刊, 2021, 03: 88-90.
[5] 李广泳, 姜广辉, 张永红等. 我国耕地撂荒机理及盘活对策研究 [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1, 34(02): 36-41.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赖勇、陈升忠系协会个人会员,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系协会副会长单位)